视频弹幕是起源于日本 Niconico,并盛行于中国大陆的一种实时字幕评论功能。除了 AcFun 和 Bilibili 这两个国内的弹幕鼻祖,现在几乎每一个往自己产品里塞视频功能的厂商或开发者,都会尝试实现弹幕功能。
由于国内大部分高质量的视频创作者几乎都集中在 Bilibili,我对这个以弹幕为主要特色的平台是有一定依赖性的。但我早就默认关闭了弹幕,已经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我早就习惯了没有弹幕的视频体验,我把弹幕功能打开之后,反而觉得不适应,而且时常带着一种会影响观看体验的眼光审视屏幕顶部飘来的文字。
我的观点是,对于大部分用户,弹幕功能是不必要的、冗余的、弊大于利的(甚至视频都是不必要的)。
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 YouTube,就算跟了短视频的风做了 YouTube Shorts,也没有跟风做弹幕功能(我怀疑这股风气只在国内吹过),似乎只有国人才对弹幕习以为常。
秉承「越是习以为常就越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今天打算以弹幕为出发点,唠一唠互联网上精神文化产品的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关系。
弹幕到底是干嘛的?
你本来在好好地观看视频,本应该专注于视频制作者、影视制片人、动画厂商为你创作的音画内容,可你偏不满足于此,一拍脑门想到:为什么不让世界另外一头的某个我不认识、也不关心的人发的,并不见得有多少智慧、也不见得有多幽默的言论展示在我的屏幕上呢?
而且一条还不够,要越多越好,让那些东西目不暇接地从我眼前闪过,即使闪过的那些语句我根本来不及看也没耐心读完,我也要让他们出现,即使代价是我没法专注我本来想看的视频内容,即使代价是不容忽视的网络吞吐量和服务器资源,即使代价是让我本来就已经令人担忧的注意力更加涣散。
我就是想让早已在重复中失去意义的文字覆盖在画面之上,让那些无名之辈亵渎创作者耗费了人力物力制作出的精良内容,就像是在路边随便拉几个陌生人,让他们在一本《红楼梦》上留下在行之间爬行的字儿。
我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合乎理性的说辞为弹幕功能正名。
诚然,弹幕功能至今依然有「供给」,就说明市场有「需求」。就算这个需求并非自发产生而是人为创造,用户也确实买账,并认为自己需要弹幕功能,至少不会思考「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弹幕功能」——弹幕又没有验证码那样烦人。
相比传统的视频和评论分离的用户界面,弹幕就只是把评论和视频内容揉杂在一起了而已。弹幕相比传统评论的特点,大概可以这样描述:
- 实时性。弹幕内容是实时的,用户在视频的某个时间点发布弹幕,其他用户也能在相同的时间点看到;而传统评论是脱离具体时间和内容的,对视频整体的评价;就算评论者想要对单个内容表达观点,也不如弹幕有实时性,其他用户可能早就忘记了评论说的是视频的哪部分内容。
- 陪伴体验。用有些不必要的浪漫主义来说,弹幕能让千万网友陪你一起看视频,屏幕上飘过去的文字似乎就是和你一起看视频的朋友说的话;你发出一条弹幕,似乎也希望有某个人能接住你的电波。
第二个点很好地引出了今天的话题「虚拟社交依赖」。
为什么互联网厂商不能好好做产品
这里的「好好做产品」指的是「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我想说的「不该干的事情」就是指「往软件产品里塞社交功能」。
没有谴责互联网大厂不会做产品的意思。从商业化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软件的社交功能能增加用户粘性,或许一个真正的产品经理还能说出一些更专业的名词来。但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只想干好自己的事情的用户,我使用的大部分非社交软件中的社交功能完全是画蛇添足。
这也是我放弃网易云音乐,开始使用 Apple Music;听播客不用小宇宙,只用 Apple Podcast 的原因之一。除了对苹果产品的设计偏好和对原生软件的用户体验偏好之外,我还喜欢他们不带强社交属性产品设计。
看视频不开弹幕,甚至不怎么看评论;听完一整张专辑之后不翻任何一首歌的评论;听完播客之后记下有启发的观点,思考不太认同的观点,也不去管其他的听众怎么想;读书之后自己写下评价,偶尔主动去平台找书评,但大多数时候也只是买前看看…… 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互联网文娱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我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第三方的观点的确能带来启发,但书本内容、文章内容、播客内容、视频内容,这些经过创作者思考和打磨的内容中传递的观点,难道不比评论区和弹幕里的有感而发更值得细细品味吗?更别提后者还包含很多追求热评的迷思和迎合大众的幽默的谄媚。
我理解大部分人上网不希望听观点也不在乎事实,娱乐也并不是什么拿不上台面的目的。但是,倘若目的是娱乐,创作者呈现的内容也能让你获得更高质量的娱乐。
评论之外的文章、播客、视频内容不少,关掉弹幕和不看评论错失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人们究竟在害怕错失什么?
冗余的社交功能背后
像弹幕这样的社交功能的「供给」反映了市场的「需求」,而市场需求也只是个人需求的总和。那么这样的个人需求,背后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得承认,我曾经也是弹幕功能的忠实用户。我甚至给我喜欢的创作者评论,问他为什么 YouTube 上发得比 Bilibili 早1,因为我想要在 Bilibili 上看其他网友的弹幕。当时的我认为「没有弹幕就没那味」。
收到白熊阿丸的赠礼时,身边有朋友好奇我从快递里拿出来的一大本书是什么,得知那是网友赠送的之后,对方有些惊讶,感叹道「我都不知道我上网能干嘛」。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我在互联网上的身份似乎是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又回想起我在中学时代的经历,与身边同学都合不来时,我基本都是在网上和素不相识的网友建立联系。如此看来,对当时的我来说,互联网上的社交功能是很重要的。
我接下来要抛出一个可能非常冒犯人的观点:依赖虚拟社交的人,可能是为了弥补现实生活中缺失的一部分社交生活。
先冒犯一下我自己,我能一直坚持写博客,一方面是我相信写作给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其他个人成长方面的益处;另一方面,我也在《我与社交媒体》里承认,博客对我而言有无法替代的社交属性,现在想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在现实中找不到能和我进行深入交流的人,或者是我在刻意回避和人的深入交流。
要特别注意的是,我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评价对虚拟社交的依赖,是否是健康的。尽管这篇文章属于「人类恶疾」这个系列,但这种「依赖」的健康与否,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取向。2
不妨把软件的社交功能看作人们「虚拟社交依赖」的一种体现,然后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现实社交的延伸
我有不少朋友会用抖音和小红书上的「同城」和「附近」功能,这能让用户看到身边人发表的内容。尽管我不怎么使用这些软件,但我时常能听到身边的人讨论自己刷到了谁谁谁(某个我们都认识的人)的抖音视频。
还有一个可能会招人厌烦的现象。尤其是一些短视频的评论区,经常会有个别用户留下这样的评论:
@XXX,快来看这个
回复:哈哈哈哈哈,有意思
尽管我还是不能理解,明明私信和转发就能做到的分享和讨论,非要挤占公共空间,但这样的现象无疑反映了现实生活在互联网上的延伸。
从这两个角度看,都能得出虚拟社交服务于现实社交需求的结论。人们在使用互联网上的社交功能时,要么是在满足现实生活中无法被满足的社交需求,无论健康与否,要么是对现实社交的直接延伸,在虚拟空间中和现实中的亲友建立联系。
恐人症
恐人症(anthrophobia)并非是专业的医学术语,我在这里提出是为了抛出另一个有些冒犯人的观点:人都有社交的需求,但社交需求不一定要通过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满足,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勇气维持现实的、强关联的人际关系,所以可能会依赖虚拟的、弱关联的社交关系。
所以就出现了矛盾的局面:互联网上人均社恐,但是这些自称社恐的网友都喜欢在虚拟的社交平台上和人打交道。
我在《十八年社恐的初窥门径》中有提出一个观点:
避免社交其实有利于自己处于群体当中,哪怕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这是人类刻在基因里的「迎合群体」的本能,因为群体代表了更高的生存几率,生存是我们原始的大脑最在乎的东西。
进一步拓展这个观点的话,就是:互联网上的弱关系也能让大脑产生「我正处于群体当中」「我被群体所接受」的感觉,进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强关系。后者才是对个体而言更重要的东西。
话说得难听一点,完全满足于虚拟社交的人似乎完全变成了自身社交需求的奴隶,而不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接触真实的人?
看完一个有意思的视频、听完一期有感触的播客、读完一篇有启发的文章、看了一本好书,除了自己思考品味,完全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不过,我身上的反骨竟被自己激发出来了,我想问:为什么一定要分享给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我究竟为什么要跟真实的人社交呢?我窝在家里不行吗?
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定义和社会需求对人的规训,似乎把 touch grass3 和「现实的社交能力」变成了一件为了做而做的事情——因为这是健康的,所以你必须这样做,否则就不健康。很少有人解释为什么。
要我解释,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和真人社交」的理由,也有不同的「拒绝和真人社交也能活下去」的理由。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每个人自己的价值取向的问题。
如果自己在家做饭,偶尔出门采购,平时在家办公,也极少需要和人合作交流,自己也觉得养养猫狗就好了、和网友吹水就好了,不需要社交,那似乎也没问题。
和厌蠢症一样,重点不在于「治好」,重点在于了解、认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真实的需求。
如果知道自己的情绪没道理,不会让厌恶情绪影响需要理性的场合下的判断,那为什么不能厌蠢?同理,如果了解并认识到自己的社交需求,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那怎样社交都可以。重点在于清晰的自我认知。
这也是《人类恶疾》这个系列者主要观点之一:承认自己有病。
我不知道怎么结尾了,我本能地想要升华主题,那我就干脆请你去读读《无事升华之瘾症》吧。
如果你觉得文章对你有帮助,可以考虑赞助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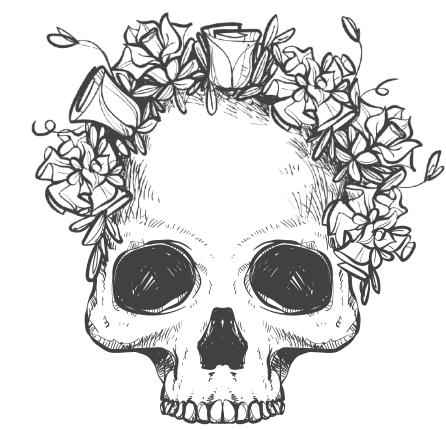
如果评论未加载,请尝试刷新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