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泼冷水的时候,把它比作了 ADHD,本来想把这次要写的现象比做 OCD(强迫症),但想不出顺口的标题,索性换了个思路。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令人安心的表象」——就我所观察到的,有不少人,尤其是年长者,十分在乎事件在表面上是否令人安心,并因此给其他人造成困扰。
我想说的不只是「话要说得好听」的强迫症,还有对负面事件的逃避和选择性忽视,从而避免解决问题;以及一些令我作呕的温情时刻,其实只是在掩盖已经没有真感情的事实。今天我就想要写写这样的现象,并试着解析背后的原因。
这是文章系列《人类恶疾》的一部分,欢迎回来。
快乐的孩子比想跳楼的孩子更值得关心
记不清楚初中还是高中,有段时间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当时我不敢让自己靠近窗户,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行为简直难以预测,幸好我还保有一部分的理智支撑我活下去。想自杀的原因我忘了,大概很复杂,也可能是想要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给家人看——我记得那时我时常想象自己躺在装满了血水的浴缸里,然后家人尖叫着跑进来的场景;我还知道,若想要达成这样的效果,最好是割腕,因为那样不容易真死。
我并不是没有求助,相反,我给出了自认为相当明确的信号。当时我在「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里转发了一条讲青少年抑郁自杀的视频,还挑选了一些关键片段截图,一并发在了群里。群里有每逢佳节都会见面的亲戚,当然也有我的父母亲,他们平日里在里面什么都聊,不可能没有人看到。然而,没有人来关心我,我的父母也没有来问过我任何相关的事情。毕竟,我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正常,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每天晚上都缩在墙角哭呢?
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七大姑八大爷们估计早就忘记了有个傻孩子在合家欢的微信群里发过那样不吉利的东西。我的父母是幸运的,因为我靠着自己内心世界的丰盈把自己拯救了回来(也或许是因为我终于离开了一个有毒的环境),然而我那爱出门喝酒鬼混的父亲,仍把我如今能被勉强称作成就的东西,完全归功于他自己且毫不愧疚,因为他也有死亡焦虑,所以把我当作他的作品,一定要安上一个自洽且华丽的说辞,让他感到自己在世界上留下了什么东西才能在晚上睡得着觉。
这些话,想必不少东亚孩子都能感同身受——「死」这个字是绝对不能说的。这样的思想甚至延续到了互联网上,人们用「si」和「鼠」来戏谑地替代死亡这个概念,致命的娱乐背后我只感受到了腐臭和可悲。
避讳死亡的父母,在自己的孩子想要自杀时会怎么办?骂他不懂事吗?有没有可能你自己就是个杀人犯(这话也不吉利,想必你是不会听的)? 更可悲的是,这样的人是没法面对自己的衰老和死亡的。由于从未正视自己的死亡焦虑,所以指望孩子能为自己创造点能留在世界上的东西,这是自然的、是人性的,但也是自私的。
话题来到「死亡」上就变得有些抽象和遥远了,我们先把话题拉回来,来谈谈另一种形式的「令人安心的表象」。
美好家庭妄想症
我和我的表哥小时候关系还不错,我的父母经常在周末把我寄养在姑妈家,那时我们几乎整个周末都在一起打游戏。我现在还很喜欢玩 Minecraft 和饥荒,其实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上了高中之后,我失去了双休日,周末去表哥家一起打游戏的惯例自然就停止了,进入大学之后更是因为长时间的断联而没了交集。
尽管我认为这段关系即使结束了,也对我个人的成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能够坦然接受,但我的父母,尤其是我那个父亲,感到非常担忧,似乎经常跟我姑妈姑父,以及其他的亲友谈起此事。大概是在我姑妈的要求下,我的表哥在某天通过 QQ 联系了我,问了问我最近在做些什么。我把当时正在做的开源项目发给了他,他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你不得教教我?」之类的话,然后就结束了话题——他学的是经济学,我学的是计算机,本来就没什么话聊了。
后来我爸也毫不避讳地在我面前和其他人表达他对我们兄弟关系的担忧,这时我的姑妈就会说「他们平时有在聊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知道 XX(我的名字)喜欢什么呀」——然而,我的表哥其实并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我们的私下交流也仅限于那一次。
除此之外,我那个父亲还试图让我和另一个我没那么熟的哥哥「增进感情」。他说我俩都在沙坪坝大学城,学校只隔了一条商业街,怎么就不能聚一聚了?他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对方,但显然对方也觉得尴尬,没有来联系我。
在这两个例子里,我的父亲和我的姑妈都在试图维护一个「美好家庭」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似乎就是他们唯一的幸福来源,一旦破灭就会发疯。「发疯」一词兴许言重了,也或许没有。记得是高中的时候,晚自习下课之后就是十点过了,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在学校外面的小吃摊买点东西回家,然后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边吃一边看点什么,好好地喘一口气。有一天晚上,我刚坐下,我的父亲就走过来,不经我允许就翻弄我的食物,张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给弟弟的呢?」。
我早就不奢求他的关心,但这话实在令人心寒且生厌。他对我的厌烦感到不满,突然就怒了,从我的书桌上抓起我的一张奖状,团成棍棒状打我的头。
因为我破坏了他对美好兄弟感情的想象,所以他要惩罚我。
后来的剧情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发怒过后便无能地哭了起来,钻进他父亲的怀里说自己这个儿子当得有多不好(然而我从未见过他有做过任何事情来尝试当个好儿子)。后来他又跟我道歉,说不该撕掉我的奖状——然而道歉有什么用呢?他打我头的时候,我含着泪的下意识反应竟然是掏出手机拨 110,因为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帮我,我的爷爷在旁边怒吼说报警有什么用,我才意识到我在民警眼里只会是一个不孝的小屁孩而已。就像那张纸上的缺口一样,有的东西是无法复原的。
我当然知道,我的父亲也有他的心理问题没能解决,但不好意思,我还忙着解决你给我留下的创伤呢,你的伤口不归我管。或许也用不着我管,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自洽——他钻进父亲怀里上演了一出知错能改的情感戏码,至少应该感动了他自己吧。
哦对,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弟弟一直默不作声地坐在房间的角落。我的父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还跟我说我弟弟多么懂事,但他从未去关心过那晚我弟弟有什么样的感受。
问题放着不管就会自己解决
小学时代,同学之间发生了点口角,只要过去一段时间,有人第一个开口讲话,之前的矛盾就当没发生过了。当然,那是因为那些小孩子的矛盾根本就构不成太大的伤害。然而,一些成年人处理家庭矛盾的方式,居然和小学生一模一样,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当矛盾和冲突发生,问题就被摆在了明面上,当争执暂告一段落,气氛变得缓和过后,人们下意识地认为问题也不存在了。这纯属放屁,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去解决问题。
矛盾冲突过后,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默认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然后赶紧重建原先的「美好氛围」,因为那样的氛围一旦消失,他们就会强迫症发作,变得无法生存。他们就像是大坝破了一个口子之后,急急忙忙地去填上缺口,然后告诉其他人大坝已经修好了,安全得很,全然不管大坝可能早就千疮百孔了。他们真的意识不到问题吗?还是单纯地懒得解决问题?
受苦比解决问题来得容易,承受不幸比享受幸福来得简单。
问题放着不管,不仅有助于快速恢复美好氛围,重建「令人安心的表象」,还有助于让自己保持「受害者」身份的认知,毕竟自己是承受不幸的那个人。如果后来继续爆发冲突,自己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坐稳「受害者」的位置,把错误都推卸给别人,就像我是那个「破坏兄弟感情的坏人」一样。换个角度看,我也在将自己「受害者化」,这整篇文章的前面部分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我也在让自己承受痛苦——不过,要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根本不会搬出这件事情来,因为他妈的我早就不在乎了。我没有指望问题放着不管就会解决,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解决问题,我只想管好自己的事。
安眠药依赖性
现实很残酷,现实中的人也很复杂。复杂的人没法塞进这些人简单的「美好生活」拼图里,他们便像小孩子一样发了疯。为了不让愿望与现实的矛盾逼得自己活不下去,他们便服用「安眠药」——选择性地忽略「不吉利」「不好」的东西,骗自己放着不管的问题会自己解决,时不时催眠自己进入受害者人设、上演各种戏码试图达成自洽…… 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反应过来,自己一直活在不真实的世界里。
如果他们真的反应了过来,想必会接受不了冲击而变得想要自杀吧?到了那个时候,忽略不管各种求救信号的又会是谁呢?
毕竟,这种自我屏蔽大概是会代际遗传的。尽管我对别人的生活不太关心,但我注意到班上的一位内倾型同学,跟室友和其他同学的关系不太好。他会因为课间教室太吵,一个人跑到走廊上做题。有一次他脸涨得通红地闯进我的寝室,跟我的一个室友说他的室友不给他开门,他激动地差点要从我们的阳台上翻过去,因为他所在的隔壁寝室灯火通明,他不相信里面没有人。闹剧结束过后,我的那个室友自言自语道:怎么回事,兴许是他们没听到吧。我认为他在创造一种「美好和谐的表象」,因为他拒绝把同学想象成会排挤和霸凌室友的恶人。
当有人试图破坏他的想象时,他同样会生气。我和其他室友选了不同的课程,他会好心地在早上离开时提醒我起床,问我有没有课,我当然是感谢他的。然而,当另一个室友随口说了一句「他出不出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便用责备的语气说「我去,你这话说得,毕竟是室友啊……」。他的语气和平时明显不同,我认为原因就是有人破坏了他的「美好室友关系想象」。
对于个体来说,依赖于想象的「安眠药」只能麻痹自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幻想总有一天会破灭的。当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个体突然惊醒,意识到自己的关系并没有幻想中的那般和谐时,便会发疯,责备任何戳破他幻想的人。此时,这种「安眠药」依赖性影响的就不只是个体自身了,还有他身边所有与他处于同一关系下的人。
回到标题「安眠药也有致死量」,我们来谈谈「令人安心的表象」这一意淫对象的致死量是什么。当幻想在认知和经验中达到一定比例,个体对现实的认知将极大程度地失真。对于一个充满了对别人的期望(例如对兄弟亲、兄弟好的期望)的人,他没法只靠自己达成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但要靠别人,又不肯自己多出面,甚至连自己的亲密关系都维持得一团糟。
由于自己又懒又蠢还既要又要,要缩短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只能将幻想代入现实,并拼命地维护这个幻想,在受到现实冲击时忽略事实,在有人破坏时发疯,责备或者作为权威惩罚对方。
令人发疯的是自己,从来不是别人
投射
投射(Projection)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指人们常常将自己的不安等情绪代入到别人身上,下意识地否认自身的不良动机、欲望、行为,并将其怪罪于外界。
这一点在许多霸凌者身上很常见,一些人认为霸凌者欺负弱小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不安,因为不想被认为是弱小的,所以将「弱小」这一形象强加在别人身上,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人骂你「你这样以后只能孤独终老」,那很有可能说明他自己很害怕「孤独终老」。
简单来说,投射就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属性设定在别人身上,并且会将自己投射的那部分自我误认为是别人而非自己,通常是为了达成某种自洽。
Sources: Psychological projection - Wikipedia
当有人的美好生活幻想对其他人造成了负面影响,就极有可能是投射机制在作祟。我的父亲只有一个姐姐,在那个二胎被禁止的年代,他作为一个「躲」着生下来的儿子,受到了不少优待,但我想他也因为「躲」而缺乏一种归属感,并对此感到不安。所以当他组建家庭时,他病态般地想要在家人身上看到那种归属感和忠诚。
过年回家的某次聚餐,我和表哥久违地又在一起打了会游戏,当我们来到客厅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父亲一直笑着盯着我俩一起下楼的身影,因为我满足了他对美好兄弟感情的一点点幻想。他从来没有对我这样笑过,那场面只让我感到诡异和不适。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是和我表哥勾肩搭背、有说有笑地走下楼梯,那个雄风不再的中年男人大概会爆发出射精一般的快感。
我不愿意只为了讨我父亲开心而培养兄弟感情,因为那并不能满足我自己,而只是满足了他投射在我身上的那一部分「他自己」。他越是这样希望,我就越是对兄弟感情这事感到不适。
「安眠药」成瘾者将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别人,而能够满足他幻想的那些人,也不过是在为了这个病人而活,实在可悲。当幻想破灭要发疯时,这病人也并不是在气别人,只是在气他投射的那一部分自我。到头来,无论他如何暴怒、殴打、尖叫、哭泣、跪倒在地,都只是气不过自己而已。如果你不是心理治疗师,也并不发自内心地关心这种人,那就跑得离他们远一点。
但我想,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幻想,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自知的程度不同而已。「令人安心的表象」问题在于个体期望问题无需自己亲自动手解决,期望别人来满足他的愿望,并对违背自己愿望的人实施严厉惩罚。这显然可以用「巨婴」来形容了。有巨婴倾向的人若是要自救,我想可以参考阿德勒心理学的「课题分离」概念。
课题分离
课题分离是阿德勒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阿德勒认为的、人际交往中应当遵守的法则。要区分一件事是谁的课题,可以思考「这件事情最终影响的是谁?」,例如孩子的学业情况最终影响的是孩子自己,而非父母,那么读书这件事情就是孩子自己的课题,父母原则上不应该干涉。
在人际交往中,分清楚每件事情是谁的课题,并不干涉其他人的课题,就叫做课题分离。阿德勒认为人际交往中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干涉其他人的课题导致的。阿德勒认为「可以带马儿去河边,但不能强迫马喝水」。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课题,学业是孩子的课题;提供物质基础和鼓励是父母的课题,这不一定要干涉孩子自己读书的课题。如果能在人际交往中做到课题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会大大减少。
Source: 《被讨厌的勇气》[日] 岸见一郎
要意识到「满足自己的美好生活幻想」是自己的课题,需要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将自我投射在其他人身上,并惩罚那些不服从自己意淫的人。投射是无意识的,但意识到自己无意识的举动,就是非常关键的解决问题的开端。
最后
这篇文章稍微长了些,感谢你耐心读到这里!我有段时间没更新《人类恶疾》这个系列,现在终于找回了感觉,这篇文章也是目前为止最符合我对「人类恶疾」这个标题的期望的一篇文章。
接下来我可能会写一写「仓鼠症」和别的什么东西,以及,「令人安心的表象」可能并不只限于个体,一些群体也会出台规则,用权威维护一个表象(例如运动会必须严格到勤,然而场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更谈不上关心到愿意大喊加油,于是和室友玩了一下午的 Uno),等我收集到足够的样本过后,兴许也会再写一写。
尽管这个系列的视角有些丑陋且尖锐,但我习惯观察他人,心理学知识也非常有意思,分析这些现象也有助于我认识自己,兴许也能给正在读文章的你一些启示。
回见!
如果你觉得文章对你有帮助,可以考虑赞助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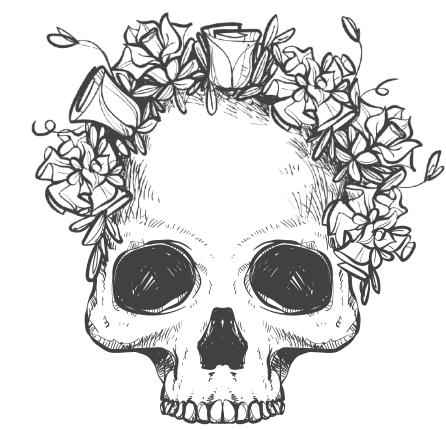
如果评论未加载,请尝试刷新页面
你也可以加入本站的 Telegram 群组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