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的饭桌上总是很无聊,向来不喜欢玩手游的我看完了 RSS 阅读器里所有的更新,不想刷短视频,无奈打开 App Store 搜索以前玩过的《元气骑士》。还没熟悉操作,就听到旁边的亲戚开始讨论「手机害人」的事情。1
第一次听长辈说电子设备害人,大概是在初中。我爸向来喜欢折腾各种新奇的东西(我大概遗传了吧),当时他买了一台小米的平板电脑,他不用的时候我就一直抱着玩,后来我爸喜新厌旧,那台设备基本上不离我手了。
我不记得我当时用它来做了些什么,但关于那台小米平板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我用它存了我第一个暗恋对象的照片,二是有一次我拿着它从房间里走出来,撞见了我妈嫌弃的表情,她用埋怨的语气讲道:「嘞东西买起来才害人哦」2
另外一次有关使用电子设备被嫌弃的回忆,也是初中,又是我爸买的东西,我记得那是一台 MacBook Air,还是带信仰灯的老款。当时我在家里用他听歌,一边听一边唱,结果一抬头看到我妈站在屋子正中央盯着我,我吓得直接把笔记本盒盖了,满脸通红地看着她,她的眼神里也写满了怨气。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有多尴尬。
小孩子和电子设备这两个东西被放在一起,就像是把蛇放进了伊甸园。即使是到了会有家长专门把小孩子送去学计算机编程的这个时代3,电子设备依然被认为是害人的东西。
我并不想批评任何人教育子女的方式,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家庭教育者为我示范什么样的家教是好的家教,我也不打算生儿育女,更不会研究家庭教育相关的话题,可以说,我对教育小孩这件事情毫无兴趣,更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指责谁,我只是想探究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到电子设备犹如谈虎色变?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不理解」也不愿意去理解,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做出「电子设备害人」这般言论的,往往是中老年人。
有很多人和我讨论如何处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时,会提到一个观点「父母年纪大了,想法和思维方式没那么容易改变」,我当然认可,可我觉得「没那么容易改变想法和思维方式」与年纪关系不大。我认为所有人都不愿意改变已有的认知,先入为主是人类思维的惯性,这在行为经济学上叫「自我羊群效应」。
既然与年龄无关,那为什么被认为死板的往往是中老年人?讨论中老年人思维的那群人,往往是年轻人,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的思想差异本来就很大,所以更容易产生思想上的矛盾。当这种矛盾出现时,双方都不愿意改变已有的认知,只不过,在年轻人这边,老年人变成了「死板」;在老年人那边,年轻人变成了「不懂事」。
所以,并非是老年人更死板,而是两个年龄群体之间都不愿意互相理解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并没有一上来就批评那些对电子设备做出片面评价的亲戚们(尽管我确实有些不爽),我知道他们那样做是因为「不理解」。如果我以维护自己的姿态做出反抗,我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不理解」——我怎么用电子产品关你什么事?
说到这里,话题其实已经从「电子设备害人」跳出来了,大部分让年轻人急得跳脚的长辈的行为,其实都是「不理解」加上自我羊群效应导致的,而且这是双向的。老年人不理解年轻人的行为,所以冠上一个不好听的名号进行批评;年轻人不理解老年人的批评,所以也明里暗里地反抗(春节期间短视频平台上的很多声音都是例子)。
第二个原因,是生活环境不同导致的经验不同,又因为信念是通过经验建立起来的,不同的经验又导致了信念的差异,相信不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就是容易发生矛盾,尤其是在双方都互不相让,无法设身处地思考的情况下。
在《阈限思维》这本书里,作者将信念的产生过程分为几层:首先是经验,过去的和现在所接触的人和事构成了经验;再上一层是注意力,也就是在自己接触到的东西、所拥有的经验中,自己注意到了哪些;注意力之上是判断和理论,也就是通过洞察得到了某种结论;最上面就是信仰,如果个体通过某种方式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和理论,那么信仰就会被加固。
年长者大部分的生活经验都来自一个电子设备尚未普及,所有人都勤奋地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时代;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两三台设备,在学校和职场卷死都不一定保得住饭碗的时代。
年长者的信仰在过去几十年的行动和观察中得到了反复验证,即使时过境迁,能推翻他们信念的观察相对较少,而且他们也很少通过行动再验证自己的信念了。生活经验的鸿沟,确实难以跨越。
第三个原因,是视角的差异。对我来说,在没有同龄人的饭桌上不能进行会让我感到愉悦的对话,我也没有带一本书来读,所以就只能通过电子设备来杀时间。在年长者的眼里,他身边都是熟悉的人,有话聊,而桌上只有那几个小屁孩不说话,自顾自地玩手机,很不利于家族团结,应该批评。
大部分人不习惯切换视角来审视问题,就像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弟弟可以和另一个男孩在餐桌上肆无忌惮地边打游戏边大叫,其他长辈也不能将他们一起玩游戏的行为视作一种「兄弟之间增进情感的交流」,如果要接受审判,这两个小孩子大概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
你不能逼人们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就像你妈让你去厨房找一个东西,你听到她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喊大叫,但她怎么喊都不能让你在你不熟悉的地方找到一个还没你巴掌大的东西。
当然,解决方案也不是没有,喊「就在柜子里面啊!」或许没用,但喊「在柜台右边的第二个抽屉的最里面」是有用的。消除视角所带来的信息差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描述自己所知道的。
这同时也是解决前两个问题的方案,清楚的沟通可以解决不理解的问题,可以一定程度上补齐生活经验的差异,还有刚才说的,消除视角带来的信息差。
但清晰的沟通很累人,不只是要多说很多话,还要思考,如何措辞才能让对方理解。不过,最要命的难题,应该是「自己费脑子又费口舌地讲,但对方捂住耳朵说『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尽管没有我描述得这般小孩子脾气,但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长辈就是有一句话堵住晚辈嘴的权利;更有甚者,禁言之后还要自己不停输出,也不管听话人能不能理解、在不在乎、愿不愿意听。
一个表达者除了要有内容、有说话技巧,还要找对自己的观众。饭桌上偶尔见一次的亲戚,还是不要管为好,毕竟没说服会被群起而攻之,说服了也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这个苦还是别吃了。
这篇文章主要想表达的,是在遇到自己觉得不可理喻的人和事面前,放下「我不理解」的执念,尝试思考视角、生活经验的差异,以尽可能理智的角度分析对方为什么会这样想。就算不反驳对方,也是比「真是开了眼」和「见识了人类的生物多样性」更有用的。在收集人类样本和案例的时候4,尝试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兴许是最有用的。
当然,我也没说抱怨是错的,只是理性上没有用处而已,但感性上能带来莫大的情绪价值。对傻逼的言论一顿分析,找出上千个逻辑漏洞,都不如骂一句「他妈的」来的过瘾。
如果你觉得文章对你有帮助,可以考虑赞助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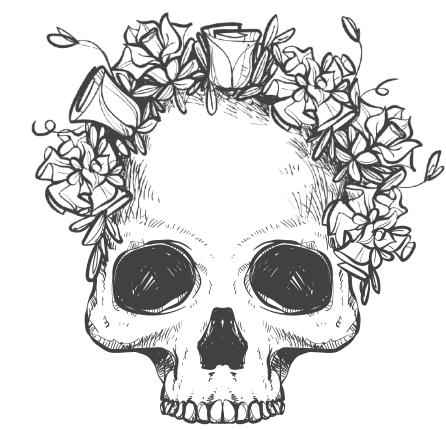
如果评论未加载,请尝试刷新页面